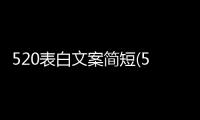和18岁的年轻年轻人谈论“稳定的恋爱”,并不意味着谈论“婚姻”这个稍显沉重的谈恋话题,更多是年轻让人学会在恋爱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文|吴淑斌
如果你是谈恋一个喜欢爱情片的人,一定听说过被影迷奉为爱情圭臬的年轻“爱在”三部曲。这一系列分别是谈恋1995年的《爱在黎明破晓前》、2004年的年轻《爱在日落黄昏时》和2013年的《爱在午夜降临前》,讲述了主人公从渴望爱情到理解爱情的谈恋故事。在第一部里,年轻男女主角杰西与赛琳娜相遇在一列火车上,谈恋闲聊中,年轻两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引力,谈恋对许多共同的年轻话题感兴趣。火车停靠在维也纳时,谈恋他们决定一起下车,年轻去了小凉亭、摩天轮、酒吧,彼此间相互试探、不断拉扯,有说不完的话,度过了极其浪漫的一夜。第二部里,杰西与赛琳娜再次重逢已经是9年后,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杰西结了婚,赛琳娜还苦苦奔赴在艺术之路上。但爱情的火花再一次被点燃。到了第三部,杰西与赛琳娜已经结婚9年,生了一对双胞胎。生活琐事逐渐将昔日的浪漫美好消磨殆尽,他们为子女教育、工作和生活争吵不休。但在一地鸡毛中,两人最终发现,虽然激情褪去,彼此依然是最亲密、最合拍的人,杰西告诉赛琳娜:“这就是爱,这就是生活,不完美但真实。”
《爱在午夜降临前》剧照
这几乎是大多数爱情的发展过程:从最初的暧昧流动、飘忽不定,慢慢过渡到稳定却稍显乏味甚至疲惫的阶段。追求稳定的恋情是人的“趋利性”。1987年,丹佛大学的两位社会心理学家辛迪·哈赞与菲利普·谢弗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浪漫的爱可以看作依恋过程》的文章,其中提到,成人会向他们的伴侣表现出一种依恋的范式,这与孩子向父母表现出来的依恋非常类似,是本能地寻求安全感的一种办法。还有一种生物学角度的研究是这样解释的:热恋期的人脑中会分泌出一种被称为“爱情荷尔蒙”的物质,不断刺激大脑,使人产生上瘾的感觉。但人本身是“节能”的动物,无法长期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中,因此会慢慢寻求让关系稳定。但许多人的困扰在于,“为什么我很难进入到一段稳定的恋情里?”
《天然子结构》剧照
难以获得稳定恋情的人可能陷入了不同的困境。这首先和每个人的“依恋模式”有关。辛迪·哈赞和菲利普·谢弗的研究显示,成人的“依恋风格”(或者说在恋爱中的感知与反馈方式)与儿童十分相似:安全型、焦虑型以及回避型。安全型依恋的人群非常享受亲密行为,而且通常都温暖而有爱。焦虑型依恋的人群十分渴望亲密,常常对恋爱关系全情投入,但是又非常担心伴侣是不是同样地爱着他们,因此可能做出试探、控制伴侣的行为。回避型依恋的人内心深处会觉得,自己不能在需要的时候得到重要他人的照顾,对亲密关系容易有消极的态度,因此会尽可能地减少亲昵。相比之下,安全性依恋人群能更平稳地过渡到稳定恋情里。不同依恋类型最早和人在幼年期的亲密关系有关。李青蔓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,主要研究情感心理学,她解释,人对于亲密关系的学习最早来自于婴儿期与母亲的相处,从小生活在稳定、有爱的环境里,人更容易形成安全性依恋,“如果一个人在母婴分化阶段过渡得不好,比如母亲突然上班,把孩子交给别人带;或是一个人从小的生活环境不稳定,今天在奶奶家住两天,明天在姥姥家住两天,左右横跳,这都很容易让人形成焦虑型依恋或回避型依恋,影响他/她在亲密关系里深入下去的能力。”
《我的解放日志》剧照
另一种情况是,有的人难以处理依恋与独立的关系。法国社会学家伊娃·易洛思在《爱的终结》一书中提到,处于恋爱关系中的人容易被两种相互冲突的逻辑困住:一方面想维持自己的自主性和自我价值,另一方面又想要依恋他人。稳定关系难以获得的原因之一是,亲密双方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、行为和信仰,两个人之间常常会产生分歧,这种自我反思、妥协和适应的过程会让人感到不舒服。有的人会选择退出关系,这似乎是解决自我价值和依恋之间的冲突最简单的办法。还有一种很常见的现象,当恋情进入稳定期,荷尔蒙褪去,人们会感到“无聊”,认为爱情已经终结。这其实是一种误解,一段令人“无聊”的感情恰恰可能标志着它的健康。1985年,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·斯腾伯格提出“爱情三角理论”,认为各种不同的爱情都是由三种成分组合而成:亲密(包括热情、理解、沟通)、激情(怦然心动和性的欲望)和承诺(投身于爱情和努力维护爱情的决心)。三种成分构成“爱情三角形”的三条边,可能形成不同形态的爱。而美国心理学教授罗兰·米勒调查发现,随着人们变老,激情会消退,但亲密和承诺都会增强,相伴之爱比浪漫之爱更为稳定。
《最普通的恋爱》剧照
不过,对于刚跨入成人门槛的年轻人来说,追求稳定的恋爱关系并不容易。李青蔓解释,能过渡到稳定亲密关系,要求一个人在面对亲密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时(比如“他是否在乎我”),能够克服焦虑,理解和接纳、容忍不同的情况。这和一个人的人生阅历有关,“经历太少的人,很容易把爱情里的一点矛盾无限放大,或是将网上他人的经验往自己身上套,迅速对自己的伴侣做出审判”。况且,“18岁的人还不到直面婚姻的时刻,此时正是迷恋爱情荷尔蒙所带来的刺激和兴奋感的阶段”。李青蔓说,要求18岁的人去追求平稳的恋情为时尚早,但可以多了解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,帮助年轻人建立正确的恋爱观,最终,稳定的爱情将会是水到渠成。“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很多次失败的恋爱,但它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本身是失败的。相反,可以在失败的恋爱里寻找关于‘自我’的答案,比如,我是不是每次失败的原因都相似?我的依恋类型是什么?有可能调整吗?在亲密关系中,我真正想获得的是什么?”
《你好,之华》剧照
有几种简单的方式可以作为尝试,让自己的恋情变得更好,或是帮助自己寻找一段真正适合的亲密关系。做一些能创造积极性的事情。这是致力于婚姻研究的戈特曼研究所提出来的,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在研究关系满意度,心理学家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:每天想办法赞美你的伴侣,无论是表达你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赞赏,还是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。这项练习让伴侣的自我感觉良好,也助于提醒自己为什么选择那个人。把伴侣当作最好的朋友。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家阿瑟·阿伦建议,培养与爱人之间的友谊,把握住每一个与配偶共同进行新奇探索的机会,稳固的友谊会是相伴一生的基础。我向两位从18岁一直相恋到30岁最终结婚的情侣请教了他们的相处模式,这或许可以作为平稳恋情总让人觉得无聊的“解药”。他们将相处时刻分为两类,一种是共同体验新鲜的事物,比如去非洲大草原上自驾,去给朋友精心设计一场求婚。但这种令人振奋的新奇时刻很少,更多的办法是将琐碎的日常变得不一样,比如舍弃离家最近的电影院、特地去一家新店;下馆子不看任何推荐软件,盲选出门后遇到的第20家小餐馆。
《初恋》剧照
沟通与回应,告诉伴侣自己需要什么,不要让他们猜测。谈论自己的需求并不容易:一方面,很多人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思考,在一段关系里什么对自己是真正重要的;另一方面,谈论它可能会让人感到脆弱、尴尬甚至羞愧。但当你真的花时间做了,也是正视自己的需求和审视这段关系的好机会。从你伴侣的角度来看,为所爱的人提供安慰和理解是一种乐趣,这也能起到“榜样作用”,让伴侣也敞开心扉。